braf激活突变在许多癌症中被确定为过度增殖的致病决定因素。RNA敲除和复合抑制BRAF导致突变的BRAF肿瘤细胞周期阻滞和死亡,减轻了临床使用BRAF抑制剂治疗活化BRAF驱动的癌症。
我们已经确定了达拉非尼是一种选择性RAF激酶抑制剂,对多种物种的全长BRAF具有活性。虽然达拉非尼在体外抑制截断的CRAF激酶,但这并不转化到细胞培养中,因为具有CRAF依赖的MEK激活(MEK抑制剂敏感)的细胞系对达拉非尼不敏感。酶和细胞数据之间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是截断(酶测定)比全长(细胞)CRAF对抑制剂敏感性更高。

或者,细胞因子可能会改变CRAF的构象,阻止其与达拉非尼的结合。我们也不能排除细胞补偿机制的可能性,或上述所有因素的组合。我们演示了高选择性的dabrafenibBRAFV600E细胞系的80%测试和假设的相对缺乏活动(gIC50>2μM)对3BRAFV600E细胞系可能是由于额外的突变的存在(GCT细胞中PTEN,PI3K在细胞,RKO和p53在A673细胞),经内部排序。
能够驱动细胞生长/生存的蛋白的过表达,或外排泵的上调,也可以从达拉非尼抑制中拯救细胞生长。虽然达拉非尼敏感的BRAFV600E细胞系偶尔也编码其他突变,但我们认为,BRAFV600E是这些细胞中关键的致癌驱动因素。
我们证明,达拉非尼在酶和细胞水平上也对激活的BRAFV600K和BRAFV600D突变体具有活性。这一结论得到了最近的临床观察的支持,在BRAFV600D/E/K肿瘤患者对GSK2118436(dabrafenib)治疗[38]有应答。我们还观察到18株缺乏braf激活突变和含有野生型RAS的细胞株对达拉非尼有轻微的敏感性(gIC50从263nM到6.9μM)。虽然这些细胞系之间没有发现共同的突变,但我们推测,激活上游BRAF驱动因子的突变或过表达可能导致BRAF依赖的细胞增殖。此外,虽然达拉非尼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但我们不能排除可能导致达拉非尼敏感性的脱靶效应。
达拉非尼对含有激活突变体BRAF的细胞具有特异性活性。在BRAFV600E细胞中,达拉非尼以浓度依赖的方式抑制MEK和ERK激活,nM活性相似,但较低。我们证实,在BRAFV600E细胞系(A375P)中,ARAF或CRAF敲除对MAPK激活没有影响。然而,dabrafenib抑制pMEK和pERK的方式类似于BRAF耗尽,这证实了dabrafenib的靶机制,即在BRAFv600e细胞中MAPK激活是BRAF依赖的。
令人惊讶的是,ARAF或CRAF缺失降低了dabrafenib对MAPK的抑制,这表明ARAF或CRAF缺失可能会增加高活性BRAFV600E同型二聚体的形成,减少ARAF/BRAFV600E或CRAF/BRAFV600E异型二聚体的形成。或者,ARAF或CRAF的耗尽可能会导致负反馈回路的松弛。BRAFsiRNA在第4和第7巷的MEK和ERK水平略低,但在第2巷的dabrafenib单独使用时则没有,尽管它具有诱导细胞死亡的能力。然而,细胞只接触达拉非尼1小时,不足以通过凋亡降低完整的蛋白含量,而siRNA处理72小时。综上所述,这些数据明显支持达拉非尼对癌细胞中激活的突变型BRAF的特异性细胞选择性。
达拉非尼对人BRAFV600E肿瘤移植模型的体内药效学标记物调节和肿瘤生长抑制作用得到证实。当达拉非尼的循环浓度低于细胞培养抑制所需的浓度时,ERK抑制速度很快(给药后2小时),并惊人地持续(给药后第7天和第14天18小时)。这不能用药物在肿瘤中的积累来解释(数据未显示),但可能是由于循环中的活性达拉非尼代谢物的存在。在体内,通过持续的药物暴露观察到与降低肿瘤细胞生长和剂量依赖的肿瘤消退相关的MAPK信号通路抑制,支持达拉非尼的靶机制。
我们证明,达拉非尼可在编码突变RAS和野生RAF的细胞中以一种工艺依赖的方式提高pMEK和pERK,这些细胞也依赖于MAPK通路的生长(对MEK抑制敏感)。BRAF抑制剂对MAPK信号的矛盾激活已被证明依赖于RAS活性,其中只有RAF二聚体的一个成员受到抑制。因此,在hct116细胞中,dabrafenib抑制的野生型BRAF或CRAF可能以ras依赖的方式与未抑制的野生型CRAF前聚体结合,导致MAPK信号传导升高。由于我们在hct116细胞中的数据显示,BRAFsiRNA没有作用,但通过CRAFsiRNA消除了dabrafenib诱导的MAPK信号转导,这进一步支持了在活化的(突变)RAS细胞类型中,BRAF抑制剂处理后,CRAF依赖于矛盾的MAPK激活的概念。
由于达拉非尼可提高野生型BRAF细胞中的MAPK信号转导,我们推测这可能导致不受控制的皮肤细胞生长,导致异常,如使用BRAF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所观察到的鳞状细胞癌。我们使用结构类似于dabrafenib的工具化合物在大鼠模型中证明了BRAF抑制剂诱导的皮肤病变的发生,并表明与MEK抑制剂联合治疗可以防止这种病理的发生。除了降低BRAF抑制剂激活的野生型RAF细胞的生长潜力外,达拉非尼与MEK抑制剂(曲美替尼)联合使用在BRAFv600e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中显示了增强的疗效。
尽管dabrafenib政府持续30毫克/公斤(33天,43天在300毫克/公斤),观察肿瘤生长抑制只在短时间内(分别为14岁和20天),其次是肿瘤re-growth,尽管以较慢的速度比未经处理的动物,这表明抗性机制的发展在不断接触毒品。在接受300mg/kg达拉非尼治疗的动物中,循环药物在第1,70和84天的浓度和分布相似(数据未显示),这表明肿瘤的再生长不是由达拉非尼代谢的时间依赖性激活引起的。在另一项研究中(未显示),经长期达拉非尼治疗后生长的肿瘤随后对MEK抑制剂(曲美替尼)有反应,这表明本实验中达拉非尼体内耐药机制依赖于erk。其他也发现了类似的耐药性机制,包括最近发现的BRAFV600Ep61剪接变体。
不可忽视的是,可能存在脱靶机制,如原发性免疫失调,导致所观察到的BRAF抑制剂诱导的皮肤增生。然而,考虑到与不同化学系列的其他RAF抑制剂类似的结果,矛盾激活的MAPK信号似乎很有可能发挥作用。此外,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在接受RAF抑制剂和治疗的患者中,RAS突变与鳞状细胞癌/角化棘皮瘤形成之间存在关联。
因此,我们假设在临床试验中,MEK抑制剂抑制BRAF抑制剂诱导的野生型BRAF细胞生长所需的浓度也可能低于单一药物活性所需的浓度,从而降低两种抑制剂产生不良毒性的可能性,包括降低SCC发生率。为此,目前正在对黑素瘤患者进行达拉非尼(GSK2118436)和曲美替尼(GSK1120212)联合治疗的临床试验。最近一项1/2期临床试验的数据确实表明,达拉非尼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在完全单药治疗剂量下联合使用显著改善无进展生存(p<0.001)和观察到的完全或部分缓解率(p=0.03)。
此外,皮肤病变的发生也减少了,尽管无显著性(p=0.09),且发热增加。然而,综合考虑,这种组合为表达癌基因突变型BRAF的肿瘤患者提供了巨大的希望。详情请扫码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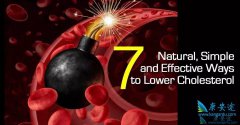








请简单描述您的疾病情况,我们会有专业的医学博士免费为您解答问题(24小时内进行电话回访)